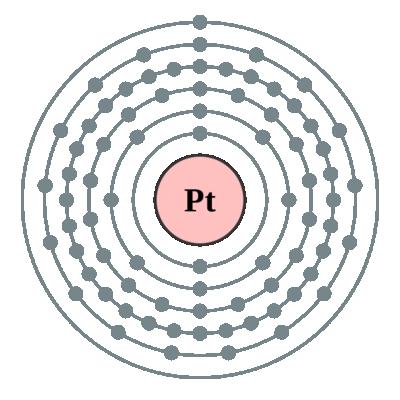内容简介
《第九个寡妇》讲述了40——80年代流传在中原农村的一个真实的传奇故事。一段纷乱复杂的痛苦历史,一场人性人伦的严峻考验。大多数人不得不多次蜕变以求苟活,愚昧朴拙的女主人公葡萄则始终恪守其最朴素的准则,则被错划为恶霸地主而判死刑的公爹匿于红薯窖几十年。王葡萄是严歌苓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超越了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小说的情节从葡萄以童养媳身份掩护公爹尽孝与作为寡妇以强烈情欲与不同男人偷欢之间的落差展开,写出了人性的灿烂,体现了民间大地真正的能量和本原。
四0-八0年代流传在中原农村的一个真实的传奇故事。一段纷乱复杂的痛苦历史,一场人性人伦的严峻考验。大多数人不得不多次蜕变以求苟活,愚昧朴拙的女主人公葡萄则始终恪守其最朴素的准则,则被错划为恶霸地主而判死刑的公爹匿于红薯窖几十年。王葡萄是严歌苓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超越了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小说的情节从葡萄以童养媳身份掩护公爹尽孝与作为寡妇以强烈情欲与不同男人偷欢之间的落差展开,写出了人性的灿烂,体现了民间大地真正的能量和本原。[1]
原文摘录
在侏儒们眼里,葡萄高大完美、拖着两条辫子的背影渐渐下坡,走远。开始还剩个上半身,然后就只剩个头顶。再一会儿,他们只能看见那大风车,空空地转着。[2]
创作背景
《第九个寡妇》是严歌苓历时5年创作的长篇,取材于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河南的真实事件。
因为严歌苓听到她前夫的大哥讲过的一个发生在河南西华县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是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地主藏在地窖的事情被发现了,这个地主出来以后就吓死了,自己连病带吓死在监狱里了,这种结局严歌苓不太喜欢,就改成了现在小说的结局。严歌苓为了《第九个寡妇》这个故事还到前夫的父亲李准的老家农村生活。
河南还有两个这样的故事,类似的,一个藏的不是公公,是一个姐姐藏的弟弟,另外一个是全家人藏的老父亲,当然跟严歌苓这个故事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基本上是相同的,后来就说生产队长和村里的一些人知道地主藏在地窖多年的事情,也帮着一起障眼法,这些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严歌苓觉得这个故事本身是带有很强烈的戏剧性。
人物形象
王葡萄
小说中的王葡萄,是一个忍辱负重,而又单纯执著的人物,有论者称其以“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超越了人世间的一切利害之争”。
葡萄皮有颜色,有韧度,娇嫩、剔透、坚韧,这同样契合王葡萄给人的外在印象。王葡萄是位娇嫩欲滴的寡妇:她的背是紧的,腰肢是会扭秧歌的,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全身没有一处败笔、一处附庸,举手投足充满恰到好处的风致。而寡妇这个开放性的身份更是给人以无穷的暧昧想象和引申,“寡妇门前多是非”,更何况是一位年龄刚好的风韵少妇!王葡萄所处的环境实在够得上凶险:灾年乱世,公公犯死罪,情人们心怀鬼胎,她需要动用无穷的勇气和智慧去抵挡窥视与怀疑、骚扰和挑衅。
作者本应让王葡萄把院门紧闭,自个儿韬光养晦,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历史事件和政治谲诡,史屯的一个普通的寡妇应该身穿缁衣、头戴紊花,冷眼旁观以求自保的。可王葡萄却迎难而上,不避凶险,尽显本真。小说借用不同人的眼睛反复强调王葡萄的本真,而她的眼睛,更成为窥视她单质内在的捷径。
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形象与民间地母神的形象的合二为一,王葡萄的形象并不是孤立地出现在小说的艺术世界,也不是孤立地出现在中原大地上,小说里的民间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它的藏污纳垢特性首先现在弥漫于民间的邪恶的文化心理,譬如嫉妒、冷漠、仇恨、疯狂,等等,但是在政治权力的无尽无止的折腾下,一切杂质都被过滤和筛去,民间被翻腾的结果是将自身所蕴藏的纯粹的一面保留下来和光大开去。葡萄救公爹义举的前提是,公爹孙二大本来就是个清白的人,他足智多谋,心胸开阔,对日常生活充满智慧,对自然万物视为同胞,对历史荣辱漠然置之。在这漫长岁月中他与媳妇构成同谋来做一场游戏,共同与历史的残酷性进行较量——究竟是谁的生命更长久。情节发展到最后,这场游戏卷入了整个村子的居民,大家似乎一起来掩护这个老人的存在,以民间的集体力量来参加这场大较量。
这当然有严歌苓对于民间世界的充分信任和乐观主义态度,故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表明了,这个村子的居民有一种仁爱超越亲情的道德传统,他们能用亲人的生命来掩护抗日的“老八”,也能担着血海似的干系来掩护一个死囚老人的生命。严歌苓的创作里总有浪漫主义的美好情愫,那些让人难忘的场景总在拓展民间的审美内涵,如老人与幼豹相濡以沫的感情交流,又如那群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侏儒,仿佛从大地深处钻出来的土行孙,受了天命来保护善良的人们。葡萄把私生的儿子托付给侏儒族和老人最后在矮庙里独居的故事,或可以视为民间传说,它们不仅仅以此来缓解现实的严酷性,更主要的是拓展了艺术想象的空间,这也是当代作家创作中最缺少的艺术想象的能力。
孙怀清
太平镇镇长,也是王葡萄如同父亲一般敬仰的公公。孙怀清勤劳善良、足智多谋,既是一位值得尊重的老人(他在村里被尊称为“二大”),也是一位无辜的受难者,在他身上凝聚了中华民族的诸多传统美德。他为人性格张扬仗义,骨子里有衡量众生价值的独特法则,任何世事变迁都能坦然从容应对,是太平镇人打不断的脊梁骨。孙怀清得知侄子孙克贤要买逃黄水的小丫头王葡萄毫不犹豫出手相救,并将视葡萄为己出对她照顾有加。面对次子铁脑被葡萄意外“害死”他依然选择相信自己一手带大的“儿媳”,用超越血缘的恩情帮助葡萄度过层层难关。他还凭借自己运送粮食的身份对山中八路军游击队鼎力支持,也救不忍杀害中国人的日本逃兵浩二于危难,更对几个用丈夫换回抗日英雄的“英雄寡妇”们时常庇佑。最终捱到抗日胜利被国民党当做汉奸陷害入狱后看空世事准备英勇赴死。
孙少勇
孙少勇是孙怀清之子,是一个完完全全投入生活的人,他以自己“循规蹈矩”的行动和形象在生活中占据了一个确定的位置,例如他为了顺应形势,主动上交父亲的财产,主动要求枪毙自己的“恶霸”父亲;为了儿子“挺”与只知工作的干部妻子离婚。他是一个以常态消融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通人形象,理智、清醒、审时度势,以蜕变苟活于风云变幻的人生考验中。
作者简介
严歌苓,女,1986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1989年赴美留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扶桑》《人寰》《雌性的草地》等。短篇小说《天浴》《少女小渔》《女房东》等。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白蛇》《谁家有女初长成》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多部作品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最近几年的有《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3]
作品赏析
作品主题
在《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一生均处往社会最底层。她所生活的从抗日战争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是人民贫闲国家动荡的几十年。即使面临如此困境,作者仍然乐观地视生活为上天对人类的恩赐;面对苦难,她没有去写人们如何被苦难所压倒,而是描写为苦难所磨砺出来的韧性。自然界自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人要生存就不能违背它,而是要顺应它,与其和谐共处,这就是自然的法则是天道。正如《管子·形势》所言:“其功顺天者天助也,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王葡萄顺天而没有向苦难抗争,也没有在困难面前一蹶不振。
在她的一生中,只有活下去是天大的事儿。对于活下去,她拥有最高涨的热情、最坚定的态度和最强悍的做法。纷乱变化的世事都不能影响她内心的宁静和对活下去的渴望,她那颗混沌未开的如水晶般的心永远做着最直观的判断:不是不苦,不是不难,不是不能一死了之。但,她的心,就是那广袤的大地,可以包容一切。有了如此顺应自然的对生命渴望,就没有什么难关不能渡过了。
在那个饥荒年代,作为一个寡妇,她不仅没让自己饿死,而且还让公公二大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期,这就是生存的本能,也是她自适和谐的必然。“对她来说,世上没有愁人的事。二大看着她颠晃的后脑勺。她和他咋这么像呢?好赖都愿意活着。”山归根结底,人生命中最后的、最自然本质的欲望就是生存,要生存便要使心灵顺应自然、适应社会。要想得开、看得开,才能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为了自适,她只认干活,手脚从没有闲的时候。她专心喂猪,后来成了劳动模范,全省的人都来向她取经;大炼钢铁的时候,为了保住锅,她竟然撒泼打混。
因为她始终有一个信念:只有锅在,只要能干活,她和二大才能活;农闲的时候她也不闲着,打柴、烧煤、刷地窖,为的就是活着;把她与少勇的儿子送给侏儒抚养,这也是顺应自然热爱生命的和谐之举。在她的人生哲学看来,没有什么事能比活着更重要,然而以她一己之力却无法达到使儿子生存下去的目的。在她看来,骨肉之情与完整地活着相比,当然是后者更为重要。王葡萄不傻,她只是按照自己的心做事。她不仅自己要生存,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活得更好。
王葡萄是严歌苓所塑造的一个“地母”式形象,然而这并不影响她对王葡萄爱情的赞美。因为她把王葡萄的一切都建构在“比于赤子”的身心和谐的本能之上。“寡妇门前是非多”,寡妇的爱情向来为中国传统道德所诟病,并且总是被贴上淫秽与道德败坏的标签。然而,尽管“不贞”成为许多人诟病王葡萄的理由,却仍然无法遮蔽她“地母”形象的光辉。问题的实质在于,“贞洁”概念如同“阶级”、“地主恶霸”一样,根本没有被王葡萄认同,她是一个未被世俗感染的人。在她身上,有一种“一切都来自自然的、本性的、非教育、非宗教的生命的本体”即生命原始状态,这当然也包括与男人们的关系。在描写女性时,作者一再用到“愚昧”、“蛮荒”等词汇。“因为只有在那混沌刚开的瞬间,男人看到的只是女人——那个纯粹的生物个体,女人亦然。在王葡萄那里,男女之情是一种原始的激情,是未经人类社会文明污染的纯生物式的,不夹杂现代文明熏染——金钱、地位、名望追求的最纯粹而真诚的人类本能式的需求。”
小说的情节从葡萄以童养媳身份掩护公爹尽孝与作为寡妇以强烈情欲与不同男人偷欢之间的落差展开,写出了人性的灿烂。如果以民间传统伦理为其心理动机来解释未免失之于简单,同样的道德伦理在男女性爱方面似乎对葡萄毫无束缚。葡萄为掩护公爹而放弃与小叔结婚,公爹为媳妇的婚事而悄然离家,都有人性的严峻考验。但是当公爹出走,葡萄若有所失:她成了没爹的娃了。于是,最终还是女儿性战胜了一切,她把公爹又找了回来。但作家也没有刻意渲染她身上的恋父情结,而是把恋父情结升华到对父亲的无微不至的照顾,转化成伟大的母性。所以在葡萄的身上,作为儿媳爱护公爹与作为女性需要男人的爱两者是相统一的,都是出于生命的本原的需要,人类的爱的本能、正义的本能和伟大母性的自我牺牲的本能高度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民间大地的真正的能量和本质。
政治合法性
政治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民间伦理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的,正是因为保障了民间伦理的逻辑,共产党才得到了民心,获得了力量。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看,《第九个寡妇》中民间伦理的合法性,也论证了孙怀清的“政治”的合法性,在这里他无疑代表的是一种地主的立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也就是“地主”翻身的历史,他们从剥削、压迫者,一变而成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化身。地主在文学中翻身当家做主人,现实中农民则饱受压迫,其中可以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第九个寡妇》可以看作不同阶层在时代中命运翻转的寓言。
艺术特色
象征隐喻
小说的女主人公取名“葡萄”,以干燥的环境下生长出甜蜜多汁的果实,影射了主人公的女性体味,含有丰富的象征寓意。王葡萄是一个血肉丰满的农村妇女,她身上突出的特点是以女儿性与妻性来丰满其母性形象。前两种是作为女人的性格特征,而后一种则暗喻其作为地母之神的神性。
作者在小说中以王葡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琴师朱梅的口l吻,道出了作为水果的葡萄和主人公王葡萄性质的暗合:葡萄这个女人“就是一颗葡萄,一碰尽是甜水儿”。葡萄成为由外而内地解读、剖析小说女主人公王葡萄的一把金钥匙。葡萄和王葡萄遥相呼应,互相喻指,其互文关系耐人寻味。
王葡萄和葡萄之间的隐喻关系既巧合又贴切,王葡萄在故事开头就无可争辩地被叫做葡萄,坚定实践生命哲学的王葡萄在史屯算得上是一个神话,可能真实的王葡萄远不及文本中的那样幸运,真实的王葡萄也不会整合诸多讨巧的要素,但严歌苓就是执著地要绘出她心目中的王葡萄——一个人间的地母娘娘、剪迷魂阵窗花的祖奶奶,她整合了严歌苓的理想主义和生命哲学,使之成为经典的深具雌性、母性特质的女性形象。
小说中地窖与夹壁也不过是一个隐喻,它通过对另一空问的生存状况的揭示,指出现实空间的非正义性,从而为历史的转折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在不同的编码系统中,地窖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意义。
叙事
小说对以往的历史进行了重述,对以往的历史观也做了颠覆,在其视野中,1950—1970年代是对象征着勤劳、善良、正义的“二大”加以镇压,使其在地下“变成鬼”、无法见到天日的时期,也是蔡琥珀、春喜等人不近人情地搞“合作化”的时期,小说同情与关怀的对象,与以往描写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的小说完全相反。作者同情的对象,用过去的话说,是“地主”孙怀清和“落后群众”王葡萄。
语言特点
在《第九个寡妇》中,严歌苓用极其简洁的笔墨对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村和社会所作的跳跃性但又能揭示时代本质的描述。小说的第九章写到八个“英雄寡妇”之一,当过史屯公社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后来被解职回乡的蔡琥珀“又回县里,解放了”时,有这么一句精辟的评论:“解放了这个,就会打倒那个。想解放谁,得先打倒谁。”这话不管是王葡萄说的,还是孙二大说的,都相当经典,它点破这几十年来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斗来斗去的本质,语言虽然简洁、平实,却富于概括性和哲理性。这正是严歌苓小说语言的特点。
可以这么说,严歌苓的语言足越来越老到,越来越简洁了,也是越来越有弹性和表现力了。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家钟嵘把“省净”定为文体最高的审美境界,是很值得玩味的。“省净”就是简洁明净,是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严歌苓在《第九个寡妇》这部长篇小说中,只用二十八万字就写出一段相当复杂的人性的历史,叙说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农村的变迁,文体可谓相当“省净”了。这一点,可能正是严歌苓小说艺术魅力的一种表现。
作品评价
这一部小说,品相令我刮目相看也!——中国影视编剧、作家梁晓声
这部小说既有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又有人们所熟悉的红色记忆,为文学提供了一种后革命叙事的可能性。——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贺绍俊